王贵祥:建筑必然跟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态有关系
来源:网友so投稿 2014-10-17
编者按:香港学者朱涛出版了《梁思成和他的时代》一书,作者称“以大量新史料追溯梁思成的心路历程,探讨中国现当代建筑发展与政权更迭和政治运动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月初的理想国沙龙上,其发表观点认为梁思成的研究存在“借鉴”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部分,引起行业内的争论。
为了还原事实,针对如何理性公正对待梁思成林徽因先生当年的学术成就等话题,记者专访了梁思成先生的再传弟子、原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王贵祥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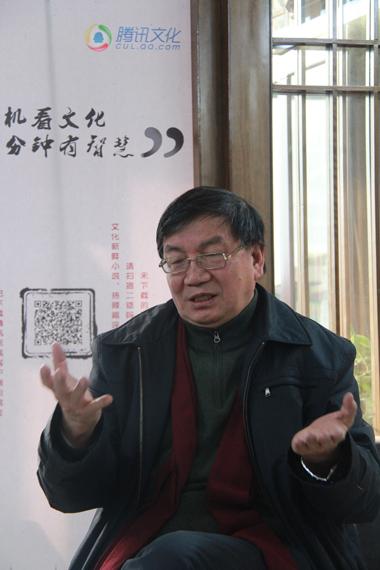
王贵祥教授
腾讯文化: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按照朱涛这个观点也同样可以评论日本写的建筑文章是大量“借鉴”了西方、欧美的东西?
王贵祥:无疑的,因为在写建筑史的时候肯定要看西方的东西,但是遗憾的是伊东忠太《支那建筑史》整本书里面没有注明一个出处。我手边有一本伊东忠太的《中国建筑史》,其中没有注明任何出处,也没有说其中的观点是从哪儿来的,参考书目也没有。这一点我们不能苛责古人,当时的学术刚刚向西方开放,日本和中国都在向西方看,那时候没有那么强烈的规范化。这一点如果要批评,是否首先应该批评伊东呢?此外还有一点,我不理解,朱涛和《新京报》为什么喜欢用《支那建筑史》这个书名?中文译本是《中国建筑史》,而他们直到现在还偏要用《支那建筑史》这个书名,他们是不是更喜欢这个具有辱华意义的词呢?这种歧视性的语言他们听着就那么舒服吗?
另外,比如说中国古人的文章也经常借用典故,但是从来不写出处,这是中国古人的习惯。“五四”以后的文人,包括鲁迅的书里面,也往往没有一条一条地注明出处,这个学术习惯是后来慢慢才逐渐被引起重视的。一定要拿一个二十一世纪大家都熟悉的规范去套二十世纪初的文章,去套一百年以前人的学术规范,要求他们像现在一样,这可能吗?何况人家也没有抄,人家是自己重新写的。在逻辑上也没有发现什么联系。这种苛责式的思维令人十分奇怪。即使受了西方建筑教育影响,参照西方建筑史的做法,中国人创造了中国自己的建筑史就错了吗?难道这个建筑史只能由弗莱彻尔或伊东忠太来写吗?这个话变成了,如果伊东忠太来写就是对的,梁思成写就是错的?什么道理?何况我认为对梁思成的这两个重要贡献,大家都没有意识到,如果梁思成不去这么紧迫地研究,中国建筑史没有这么多实例的支持,那现在可能还是日本人的体系,伊东忠太的体系,难道这样,朱涛或者《新京报》记者们就安心了吗?实际上,日本人认为中国建筑的木结构实例,最早到1038年,这之前,就没有东西了,写不出个所以然了,所以只能写到北魏或隋,主要写一写石窟寺。此后唐宋元明清的东西太多,他们没法理出一个头绪。
另外的问题是,梁思成如果不把这两本天书清《工程工部做法营造则例》和宋《营造法式》解释清楚,我们现在看中国古建筑,还是一堆糊里糊涂的东西。也可能后人能解释,但是起码要滞后好几十年,而梁思成是开拓者、是先驱。
腾讯文化:您做了建筑史研究40多年了,建筑跟政治应该不应该有关系,如果有的话应该是怎样的距离?
王贵祥:建筑作为一个大规模的社会活动,不可能脱离当时的社会政治形态。因为建筑需要动用大量的物质财富,需要决策,需要根据当时社会的需求、社会的能力去做,所以不可能(脱离)。比如历史上有皇权的时候,中心建筑是宫殿,你再批评中国建筑,它也是以宫殿为主,还有帝王陵寝、皇家园林是中国建筑的主流。中国的宗教建筑也很活跃的,在一些朝代,如南北朝、隋唐时代宗教建筑的比例很大。但是一旦政治上发生变化,就会受到冲击。比如历史上打压佛教,所谓“三武一宗之厄”,佛教建筑就受到了很大的摧残,这都是因为政治的原因。建筑这样一个大的社会物质生产劳动,跟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态不可能没有关系,说没有关系要么是乌托邦,要么是痴人说梦,(这种关系)必须是有的。
建国以后也是有的,中国人毕竟是经历了从一穷二白到现在这样一个比较好状况的过程。另外是经历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在这两个过程中,各种各样的矛盾太多、太复杂,谁也把握不住。即使是当时的领导人,有一些失误也都是有可能的,因为那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事业,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看过去,当时有当时的历史语境。当时人的一些话,拿到现在的语境中来批判,这对他们不公平。(本文来自腾讯文化访谈栏目“文人白话”)
发表评论
最新评论
 投稿
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