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涛:当代设计师仍被政治权力裹挟
来源:匿名网友投稿 2014-1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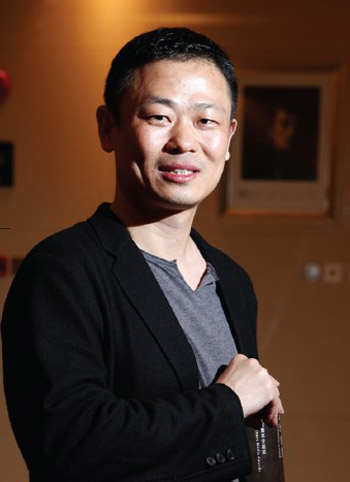
建筑师朱涛
“仅仅让我们远远地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做一番鸟瞰,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浪费惊人的世纪:浪费掉了机遇,浪费掉了资源,也浪费掉了生命。在外侮入侵和占领的苦难与内政如此的无道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怎么可能会有目标明确的国家建设?在大众的贫敝被某些时期里市侩的贪婪无度与另一些时期里国家的极端集权主义变得日益深重的时候,怎么可能会有平衡的经济增长?在一个长期动荡不安和审查制度严酷得令人难以想象的社会里,个人的创造活动和心智的探索怎么可能会得到普遍的展开?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故事从一开始大概就是上述悲观的看法的证明。”
这是1993年,历史学家史景迁给费慰梅所著的《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的序言开篇。这个开篇,与其说是写给梁与林,不如说是写给二十世纪以来,追寻现代中国之路的整整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数十年的生命与智慧,分秒必争地投入在应对这个民族千年未有之危机与变局上,却总是在思辩刚有眉目、论争刚有启示—整个民族现代身份的构建刚刚开始之时,就被迫卷进一场又一场结构性的历史悲剧里,左冲右突。未完成的重要讨论在更紧迫的国族危机中或者扭曲,或者中断;刚刚建立起的与世界的平等对话窗口被迫一一关闭,而每一个论争者、思想者都在历史洪流里自身难保。
思想史学者葛兆光近年回溯20世纪初知识分子构建“中国”的努力,在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等等领域,无一不看到这样没有来得及充分展开的思考。“中华民族”从哪里来?边界在哪里?它如何向现代国家“中国”转化?如何与世界交流和对话?
在建筑学领域,梁思成对“中国建筑”的构建,同样处在这样的思想史脉络中。而激发起后学者朱涛对梁思成追问的,也是各个领域的中国研究学者面临的相似问题:历史经验的断裂、理性争论的扭曲,令我们直到今天都无法在国际语境中有效地阐释自己。长期浸淫在西方建筑历史与理论里的年轻一代学者朱涛,在美国留学的日子对此深有感触:“直到今天中国建筑依然无法与世界有效对话,我们也不能有信服力地阐释自己的空间状况。为什么?”他的问题意识由此而起,并最终追溯到“中国建筑之父”梁思成。
2014年2月,建筑学者朱涛出版《梁思成与他的时代》,书中认为,梁思成和他的时代所经历的一切,不仅重要,而且还远没有结束。“重现他在西方建筑话语对中国建筑史的曲解和垄断中,在日本学者取得成就的激励下,为中国建立起一整套自主的建筑范式的求索过程,重现他的心路历程和学术选择,他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对我们今天的存在,至关重要。”
朱涛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寻找梁思成。这“问题”的来源,与一百年前,年轻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在美国留学时所面临的情境与冲击,竟有奇异的相似。
2006年,37岁的建筑师朱涛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念博士。这是他在纽约的第8年。“中国”逐渐成了这里最时髦的话题。曾在上海、深圳、珠海等地做过七年建筑设计的朱涛起先很逆反,他推掉了教授中国城市化课程的邀请,博士论文不写最熟悉的中国,偏偏选择欧洲古典建筑研究。他说,一方面“不屑于以自己的中国资源作为资本来竞争”,另一方面,则对许多外国建筑师对中国的理解失望透顶:“很多人从来没去过中国,却垄断着对中国的解释,夸夸其谈,肤浅得都不值得交流。”
就是这时,在哥大的一次讲座里,朱涛听到德国建筑师Ole Scheeren讲述在中国的经历。Scheeren是荷兰建筑师库哈斯和O-MA事务所的合伙人,他们正在设计的项目是中国CCTV新总部大楼。面对来自西方世界最常见的质疑:为CCTV设计这么一栋巨大、张扬的楼,是不是有违建筑师的伦理?Scheeren的回答听起来十分雄辩:首先,CCTV的巨大尺度不是建筑师的选择,而是业主自己决定的;其次,“在中国,修建这样的巨型建筑根本不是一个独特的当代现象,而是中国在追求现代化路上一以贯之的传统”,“中国有一种神奇的拥抱变化的能力,还有一种特殊品质:不后悔”,“中国似乎有意愿和能力,充满勇气地面对新形势,充满热情地追求进步—即使这些激进的变化有时意味着对过去状况的粗暴抹除……”
朱涛至今还记得刚听到这番言论时,血液直冲头脑的感觉,没有什么比Scheeren的话更深地刺痛他的心。对外国建筑师来说,中国是开盛大party的试验场,只要操纵好有限的知识,就可以玩得尽兴,盆满钵满,再回到西方建立起自己的“新”话语。他们很少真正关心中国问题,因为埋单的不是他们。问题只有一代一代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自己消化:生态环境、城市规划、人口就业、土地……却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点。
朱涛第一次对纽约产生了厌倦:“你看到那么多智慧堆积在这里,变成纯话语;而在中国,这么需要智慧的地方—所有的理论话题在中国都有具体的针对性,可能解决实际问题,可能促成巨大转变,但却那么少的知识积累。”
他开始大量地读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社会、政治、环境、生态的论述,并终于决定回国。“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可能带来建筑革命,而这种技术转移最可能大规模地在中国发生;前沿的城市研究可能帮助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少走弯路……”2007年接受聘书前往香港大学任教时,这是朱涛怀揣着的“中国梦”。然而不到一年之后发生的四川地震,以及紧接着的奥运工程,让他意识到,问题远比这复杂得多。
“灾难之后的反思有可能带来彻底的改变,台湾的9·21地震重建正是如此!”朱涛联合不同领域的朋友迅速行动,满怀激情要发起中国的“新校园运动”。投入巨大精力忙碌了几个月之后,一厢情愿的“新校园运动”除了修起五栋新乡村校舍外,连个泡沫都没有留下。朱涛意识到,今天中国的问题根本不在于缺少高新技术或者前沿理论,而在于缺乏均衡、理性的决策,导致资源分配不公正等社会矛盾,“而要深入理解这些矛盾,很重要的工作是展开历史性分析,恢复历史经验的连续性”。
建筑,作为耗费巨大资源、同时兼具社会功能与文化符号意义的系统工程,因为它天然的政治性,从来不能置身在历史的苦难之外。朱涛说。正是由四川地震开始,建筑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它在历史中的动态表现,超越了建筑本身的形式美学,成了他最关切的命题。
2009年,朱涛改了自己博士论文的题目,转向研究中国大跃进时期的国庆十大工程。“我意识到关于大跃进和国庆工程有两套历史知识,一部社会史和一部建筑史,这两部历史之间的鸿沟是如此巨大,让人甚至怀疑它们是否是在讲同一个时代”。“为了更充分地理解58、59年的历史瞬间,需要追溯新中国成立十年的历史。而在这一段历史里,无论分析建筑设计风潮的变化,还是建筑与社会的关系,都离不开对梁思成这一中心人物的考察。”这也正是《梁思成与他的时代》的成书缘起。
循着一个接一个问题,从西方回到中国,从当下回到历史,绕了一大圈,终于走近梁思成与他的时代。对研究者来讲,这当然不是轻松的旅程,相反,是足够痛苦与难堪的。尤其是看到梁思成和他的同仁们的经历:怀抱理想,漂洋过海求学归来,在满目疮痍的祖国带着强烈的现代化冲动建立起“中国建筑”范式;看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城市弊病,满怀希望社会主义政权可以规避这些问题,发展出美丽新世界;没想到却在1949年之后的政治运动中被冲击得七零八落……
在这个痛苦的梳理过程中,朱涛意识到,无论对梁思成本人还是他所处的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其中的重要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在今天都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和反思。而历史远没有结束,梁思成那一代建筑人所面对的建筑与社会的复杂关系,政治任意化导致建筑任意化,建筑师被权力裹挟的局面,仍在以不同的方式延续。
在书的最后,朱涛写道:“历史写作并不能为我们面临的紧迫问题提供具体答案,也不会帮我们预测未来。但它对于我们的存在至关重要。深入的中国现代建筑史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挖掘集体健忘症的根源,挑战和击破神话,解释来源和意义,重新恢复我们空间经验的连续性和共同性。”
发表评论
最新评论

 投稿
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