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利:新乡建依托旅游得以发展
来源:畅言网 2016-04-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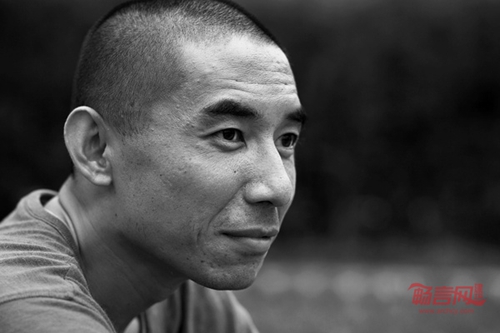
清华建筑学院院长助理、简盟工作室主持设计师 张利
2010年以后,我国越来越多的优秀建筑师开始逐渐向农村转移,我们在农村看到了最活跃的新思想和新技艺的尝试。那么,新乡土建筑在我国的发展状况究竟如何?建筑师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新乡土建筑未来发展如何?清华建筑学院院长助理张利教授分享了他的看法。
新乡土建筑兴盛的原因与趋势
建筑畅言网: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新乡土建筑”概念的由来。
张利:“新乡土建筑”在国际上一般叫“当代乡土建筑”,即Contemporary Vernacular,指的是在全球化制造与加工的背景下强调延用地方工艺、针对该地生活而建造的不可随便被移植的建筑。
Vernacular翻译成中文后变成“乡土”,似乎就一定跟农村相连,其实Vernacular在世界语境里并不意味着落后或者前工业,那些只适用于某个地段、气候和地方工艺的建筑形态都可以被叫做乡土,也就是说在北京也可以有“乡土建筑”。
建筑畅言网:新乡土建筑火热的背后是经济原因还是有其他原因?
张利:我觉得经济只是其中一方面,不排除整个社会资本的兴趣转向乡间土地,但我认为,最关键的还是大家对全球化的现代性已经有所反思,建筑师们开始自发地寻找一条不一样的道路,从而表现出对新乡土建筑的兴趣。
建筑畅言网:在您看来,经济原因是很次要的原因吗?
张利:经济原因也不能说是很次要的,但从本质上讲,西方开始重视当代乡土建筑是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战后重建完成后,大家渐渐发现那种大量复制的现代性建筑有其固有的问题,经济只能算是其中一种平行的原因。
建筑畅言网:据我了解,很多乡建项目都是旅游项目,您认为乡村作为旅游目的地吸引城里人,这个市场有多大?能持续多长时间?
张利:我也参与了一些农村项目,不仅仅是新乡土工程,有的人把它称为“新乡愁工程”。在这些项目中,无论是自下而上的,还是自上而下的,旅游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因素,因为旅游能够吸纳资本。如果没有旅游,很难从道义上真正实现对农村的援助,很难公平地实现大量资本从城市到乡间的转移,所以做成旅游项目有其必要性。
我觉得旅游只是一个开始,慢慢地会形成乡间自有文化,形成农村自我发展的经济模式,古代中国就是这样发展的。中国古时候大量的文化精品都产生于乡间,那些在朝为官的知识分子告老还乡以后,用一种更自主的方式,一边过田园生活,一边写书或完成其他作品。
其实这个问题涉及到两个“二分法”,但都不太合适。首先是“城里人”和“农村人”的二分法。广义上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城里人和农村人,只有不停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移动的人口,有的是从城里到乡村,有的是从乡村到城里,劳动力往城里来,休闲旅游则往乡村去。在现在社会发展阶段,这种情况必然存在。这是生活方式的变化,不是简单的旅游。
第二个“二分法”是“旅游”和“非旅游”。如果把所有用于非工作的、非居住的、从城里到乡间的运动都称作旅游,这种旅游与传统的旅游不太一样。一般我们认为的“旅游”是一种消费行为。实际上,现在很多从城里到乡间的移动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旅游或消费,而是到新的环境里寻找新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这种生活方式不是城里的有固定作息时间的方式,而是伴有部分农业生产,并期望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创造一些新的东西,这种现象在文化圈里比较常见。
把乡村作为旅游目的地的行为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可能有些做法会因为不适应需求而失败,比如在农村盖高楼,或者把原址上的建筑全部拆掉重建一个新的主题街区;那种过于行政指令化的、大规模的新农村建设行为到一定程度也会结束;北方有些农村做过突击性地、大规模地给农村房子贴瓷砖、刷白墙、造坡屋顶,做出所谓的民俗符号的行为,也是不可持续的。真正可持续的是对独立的农村建筑进行渐变式、有机式地建造或改造。
建筑畅言网:您刚才提到“到农村寻找新的生活方式”的人群多吗?
张利:文化界里这种人还是挺多的,这跟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告老还乡、解甲归田的情怀很接近。城市作为主要的机会提供者,机会多、效率高,但同时压力也大,资源很有限,对有些人(比如老人)来说并不是理想的生活场所,而乡村能提供现代人非常向往的生活环境。如果乡村能够建成一定的医疗体系,老人往乡村的移动规模将非常可观。
建筑畅言网:但目前涉及农村医疗的乡建项目还非常少。
张利:就像刚才说的,现在只是资本开始移动,还没真正移动到那么高的程度,因为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流转还没有完全定义好,一旦土地流转定义明晰了,自然会出现乡村医疗建设项目。
建筑畅言网:关于新乡土建筑的建设模式,有两种针锋相对的看法,一种是认为应照原样保留现有村落格局和形式,另一种则认为应该与时俱进,有所改变。您怎么看待这两种观点?
张利:前一种是”化石理论“,把一切既有的现象都以审美的方式看待,保护它,使它成为活的化石,让后人欣赏,这其实也是一种消费,而且对农村人并不公平。另一种做法又过于激进,把城里的那一套照搬到农村,只不过以更低的密度来做,也不合适。
我觉得在这两者之外,还存在第三种可能性,以原来没有的模式呈现。我们可以仔细回想一下,城市和乡村的历史都是在缓慢改变的,不会永远冻结在某一种状态里,也不能用我们自己预期的某一种未来状态进行大拆大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是可能的和被允许的,不过要符合那些居住在其间的人的想法。
建筑畅言网:找您做设计的是政府项目多还是个人项目多?找您设计的个人业主,一般持哪种观点?
张利:政府和个人都有。政府和开发商一般会希望拥有完整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我们会建议他们尽量不要动农民的宅基地,改为使用集体建设用地,比如改造废旧的乡镇企业厂房。
农民集体(比如以村为单位)请我们做设计的人中,想上楼的占了多数,他们觉得上楼的生活干净、现代,也比较方便,比平房好。我们也还是会建议他们在不修高楼的情况下实现城里的舒适度和方便、现代、卫生的生活。如果修了高楼,会把农村那种与自然相协调的、宁静的生活环境破坏殆尽。
建筑畅言网:在新乡土建筑的项目中,建筑师能做什么?能否依靠这些项目养活自己和工作室?
张利:我认为做新乡土建筑设计主要是让建筑师跳出工具理性的束缚,真正为一个地方、一种气候环境和一个局域的文化社区做一些改变。建筑师很难靠乡土建筑设计养活自己,现在我们看到的乡土资本转移毕竟是极少数的,做乡土建筑的设计师一定还有别的项目用来支持设计师的生存与发展。乡土建筑产生的利润并不高,但它是建筑师喜欢的设计形态,这也与中国的居住传统有关,大部分人都有“知识分子告老还乡”的情怀,这种情怀也不仅限于“乡愁(nostalgia)”,而是追求在一个密度相对较低的地方与自然更贴近的居住方式。
如何评价新乡土建筑项目
建筑畅言网:您会如何评价近年来建成的新乡土建筑项目?
张利:建筑一般需要经过三次判断,第一阶段是在新建成一两年内,大家会立即判断有这个建筑和没有这个建筑的好坏,此时关注的是建筑形象和外部形态、环境,以及它所带给大家的灵感;三五年后看的是建筑本身在实用性和运营上的投入,以及功能上是否牢固可靠;十年以后关注的是建筑对社区、对局部文化的影响。现在我们所见的那些新乡土建筑项目,还没有哪一个达到十年。评价当代建筑,没有必要因为年限短而不予评价,但每一个建筑都需要经过这三重评价。
比如我们正在做的山东安东卫北街网绳市场改造项目,目前由于投资行为放缓尚未实质开始。如果开始,它所面临的最后检验标准就是完工后这些商户是否还愿意留在其中,这是最关键的。
建筑畅言网:现在这些已建、在建的农村项目,我感觉只有一小部分是给当地农民用的,绝大多数并非如此,这些项目能够给当地带来什么?给当地住户带来什么?
张利:一般来讲,社会效应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上的,给他们带来经济收入和就业机会;二是环境上的,对城市来说可能是局部空气和自然环境的改善,对于农村则是卫生方面的改善,同时不损坏已有的自然环境;第三是最深层的社会文化方面的改善。项目是否能让村民们更认同现代生活的价值观,这一点短期内看不出来,但前两点基本上在建成后一两年内就可以得出评价。
现代社会对人的吸引力不可争辩地体现在经济上,经济越集中的地方,信息和机会也越集中,新乡土建筑是除了旅游之外乡村唯一能够跟城市展开一点竞争的形式。但建筑项目不是万能药,不能完全取代经济手段。
建筑畅言网:作为建筑师,您会担心自己在农村建的房子最后没有人使用吗?
张利:在大学教学的过程中,我也讲过意识形态化的建筑,道义上正确,实际上空置,即常说的“乌托邦(utopian)建筑”。在实际接触农村项目的过程中,我们往往要寻找明确的支点,证明在至少未来五年内的经济活动能在该建筑内完成,保证项目可以持续进行。对于确实没有可持续性的项目,我会建议甲方不要做。
建筑畅言网:国外的哪些新乡土建筑设计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张利:那太多了,比如上世纪70年代的埃及建筑师哈桑·法赛(Hassan Fathy)、斯里兰卡建筑师杰弗里·巴瓦,奥地利的Martin Rauch,他们做的就是非常优秀的现代乡土建筑。
关于建筑的一些讨论
建筑畅言网:您在一次采访中说过建筑不仅是在视觉上让人产生愉悦,还要在空间上让人产生自豪感。您如何通过设计让人产生自豪感?
张利:建筑艺术中有一种提法,可能每个建筑师都想做到,但往往可遇不可求,就是空间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提升人的精神,使人通过对空间的体验,不仅仅是视觉,也包括触觉、听觉、嗅觉而让人感觉美好,即通常所说的愉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Epicurus)等哲人都曾经做过这样的分析;中国古人也提出过“天人合一”,希望个人能承载天的精神,或者承载最理想的灵魂;近代的海德格尔在现象学里讲到“诗意的栖居”,其实都是一个意思,都是在说怎么通过空间提振人的自信和愉悦的状态,换句话就是“你对你是你自己,在地球的这个地方”感到自豪。
建筑畅言网:是大尺度建筑还是小尺度建筑更容易让人感到自豪?
张利:跟尺度没有完全的关系,取决于最后你的身体能够感知到的界面,有时候是小的空间有时候是大的建筑,但一定是好的建筑才能做到。
建筑畅言网:您在说的时候我脑子里就显现出“光之教堂”,还有别的宗教类建筑。
张利:我以前给学生讲课时经常用到两个例子,一个是郭沫若故居,以前是恭王府里的马厩第二进里的门廊,两边都有一个通天的小院子,郭沫若故居是把门廊改成室内,但廊子没有动,有牵牛花,可以想象一下春天坐在那种地方的感受;荷兰的多特莱赫特也有这样的房子,建于17/18世纪,房子前屋檐下种着各种花草,还有供人就座的台子。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东西方在对空间的感受方面是贯通的,人在这样的空间里就会觉得生活美好,心情愉悦,同时也觉得自己的灵魂承载了这些美好。因此,不一定是很大的、纪念性的建筑,还可以是生活中很平常的建筑。
建筑畅言网:您也说过“建筑不仅仅是技术上的事,还有很多软的东西,后者比前者更关键”,“软的东西”是指什么?
张利:一般“硬的东西”指的是实证主义,“软的东西”指的是非实证主义;“硬的东西”指的是用来建造建筑的技术和物质,“软的东西”是指经过人和物质接触的界面传达出来的精神被理解、被认知、被体验,这种东西更重要,没有人的存在和感知,这些东西都没有意义。我们不能绝对地去比较这个房子比那个房子好,认为用这样的技术盖出来的房子比用那样的技术盖出来的好,我们可以说它先进,但不能说它在建筑上好,好与不好最后都需要通过人的身体器官去感知,从而形成人对建筑的记忆,这就是“软的东西”。
换句话说,同样做混凝土建筑,可以完全按照技术合理的方式,用符合逻辑的、理性的、必要的方法建造,也可以有意地避开这些最逻辑、最理性的方法,增加非必要的东西,比如,屋顶、墙是必要的,可以做成必要的状态,但是为了让人产生更愉悦的感觉,有意地把墙做成另外的形态,甚至故意隐藏墙体保温和支撑的功能,这些就是软的东西。
发表评论
最新评论

 投稿
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