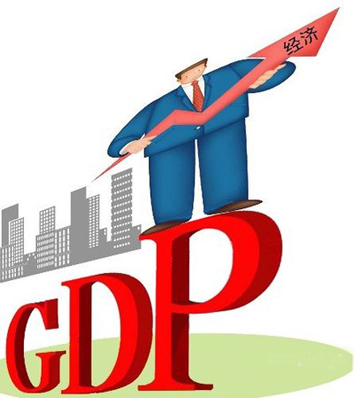袁牧:城镇化红利正逐渐耗尽
来源:凤凰网投稿 2014-07-02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总规划师 袁牧
精彩观点:
〈〈〈城镇化红利在慢慢耗尽,我们能够从中获取的利益已经越来越少。在城镇化过程中,我们过去走得太快,从未花时间去探寻方向,甚至顾不及去认识其中的问题,所以必然要用今后的十年、二十年去逐步理清和解决。
〈〈〈北京未来发展的目标是十分明确的,北京周边的天津市、河北的石家庄,都会根据这个目标来确定系列目标。毫无疑问,市场在这里面起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每一个地方政府对于自身发展和市场预期、本身所能营造的市场空间,都有自己的大盘算。
〈〈〈一种可见的情况是,一座城市的发展给国家和周边城市带来经济效益,但却没有给自己的市民带来福利。而只有给市民带来幸福感和福利,才是真正值得欣喜的事。
从2003年十六大中央将新型城镇化思路明晰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到十八大明确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路径,城镇化建设始终位于热议话题榜的前列。尽管众口纷纭,时至今日,几乎我国所有城市的城市形体、人口结构、社会意识形态等层面的深刻变革都实实在在地发生着。
不可否认,城镇化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红利,然而,这种红利是否可持续,老百姓又能否分享红利?同时,城镇化的宏观目标下,城市自身应如何合理规划?城市群、经济圈的未来又在哪里?
对此,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总规划师袁牧直言,城镇化的红利在慢慢耗尽,过去走得太快,从未花时间去探寻方向、认识问题,而随着经济列车的逐渐减速,各种问题将暴露无遗。
对于城市规划,他认为,规划的基本原则是要为未来的发展留足空间。地方政府对于自身发展和市场预期、本身所能营造的市场空间的“大盘算”要符合区域的分析研究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可能性。“一座城市的发展可能给国家和周边城市带来了经济效益,但却没有给自己的市民带来福利。而只有给市民带来幸福感和福利,才是真正值得欣喜的事。”
城镇化红利正逐渐耗尽
Q:新型城镇化新在哪里,其核心价值是什么?
袁牧:过去城镇化的整体思路是将城、乡二元对立,从乡到城人口单向流动,甚至包括土地和资源的单向流动。从人文主义出发,城镇化是人对于生活方式的重新追求,也是一个人价值观的重新定义。对于老百姓而言,不论身在城市还是乡村,都追求良好的生活状态、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这是城镇化的目的,也是对城镇化的重新理解。
Q:城镇化是否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带来了最大的红利?
袁牧:是的,但是这个红利在慢慢耗尽,我们能够从中获取的利益已经越来越少。在城镇化过程中,我们过去走得太快,从未花时间去探寻方向,甚至顾不及去认识其中的问题,所以必然要用今后的十年、二十年去逐步理清和解决。
Q:城镇化是否意味着三江平原等水源保护区、生态涵养区,随着产业化发展,有可能被破坏?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需求和当地百姓获得城市生活资源的需求,二者是否存在利益上的博弈?
袁牧:这里可能存在误区,城镇化不等于建城市,不是把三江平原变成城市。新型城镇化带来的更多是对城市人口生活状态的变化,可涉及全民。不论城、乡,都是对生活方式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转变。这样的话,即使在非城市地方,强调城乡统筹的根本目标也是缩小城乡的二元对立。
Q:城镇化过程中,政府的权利和义务边界在哪里?
袁牧:城镇最初形成于周朝,自上而下,为管理、安全和防卫而出现,整个历程都少不了政府引导,现在亦如此。政府该做什么,市场该做什么,市场是否要介入政府管理,政府是否要承担市场责任,这都是需要理清思路的。但需要明确的是政府要履行职责,切忌越位,把适当的职能和工作留给市场。
天津河北随北京打规划算盘
Q:城市数量不断增多,空间边界不断扩展使得科学的城市规划十分必要。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地方政府在城市规划方面存在着哪些误区和问题?
袁牧:中国的城市规划呈现多级化,国家是具有区域战略规划的;从国土角度出发,不论哪块区域,也不论地理环境还是社会经济发展程度,都会针对地区特点决定城市发展的宏观目标和导向。长三角、珠三角的战略发展规划,以及一些省级发展战略规划和之前做的城镇群发展战略研究,都属于区域性的战略规划。
规划是有层级关系的,每一层的规划都要符合上一层规划对这个规划所提出的一系列的指导方针和要求。城镇化的宏观目标是确定的,地方政府的发展目标要与其相吻合。例如,北京未来发展的目标是十分明确的,北京周边的天津市、河北的石家庄,都会根据这个目标来确定系列目标。毫无疑问,市场在这里面起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每一个地方政府对于自身发展和市场预期、本身所能营造的市场空间,都有自己的大盘算。
这种盘算要符合区域的分析研究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在空间上并不能达到你所规划的要求,这就出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中国所有城市的总体规划和总人口加起来,城镇化可能早已超越了百分之百,但所有城镇规划都要考虑未来发展,未来又有不确定性,这就导致要为未来的发展留足空间,这就成了规划的基本原则。
Q:北京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进行城市规划,回看过去这些年,北京的城市变迁的速度是否超出了城市规划的预期?
袁牧:城市规划是动态的,一定是随着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来调整完善和不断补充的,实际上也是对未来的远期预想。针对近期每隔一段时间会有的动态调整和发展,但完全超出预想的可能性不大。
我对中国城市未来发展保持乐观。随着经济列车的逐渐减速,各种问题暴露无遗。一个城市如果在前十年、二十年的目标导向是增速经济发展,那么,遗留在社会生活上的问题就会在未来显现。因此,政府的注意力一定会放在留有问题的区域,而我坚信他们有足够能力去解决问题,集聚现有经济力量再次投入社会经济文化建设。
Q:在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建设用地增长的同时,二线城市却在进行新城、新区建设,甚至不惜以削山、填海为手段。那么,如此广泛的新城、新区建设,是否会带来老城区的衰落?
袁牧:市场希望新区提高人气,但是我们发现,新区缺乏人气,老城市反而有活力、有人气。尽管如此,老城仍旧需要提升和改造,其变迁并不直接伴随着新城建设。从城镇化进程来看,新城人口集聚并不是城内人的变动,而是城外向城内的集聚。这种情况下,不论新区还是老区,不存在人口的内部大规模迁移问题,而是局部调整。比如,部分老城的居民搬到新城,外来人口进入老城,这就带来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但不足以造成老城的衰败。反而在欧洲这些人口较少的发达国家,如果建设新城,易造成老城空化。
珠三角因缺乏多元模式易崩溃
Q:长三角、珠三角这些区域经济发展范例,对其它区域发展借鉴的贡献意义是什么?这两个区域经济带的发展模式有什么不同?
袁牧:经济圈是一种竞合关系。就城市圈、城市群来讲,真正发育成熟的是珠三角和长三角,而京津冀尚且处于发育过程。珠三角依托当年港澳产业外移、资金外移,形成区域,是中国的一个工业园区,厂属中国,资金、老板外来,但是劳动力多来源于内地,缺乏属于自己的东西。任何一个区域的发展,都需要配备相应的技术,形成内在基础,而非单纯依靠虚幻飘渺的概念。长三角形成规模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在历史上就拥有工业基础和劳动力集群,所以在产业化过程中是自然而然地向这里集中。
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拥属于自己的东西:劳动力是自己的,熟练的工人是自己的;大量的技术,包括产业基础是自己的;地方文化技术、科学发展、人才力量、资金力量能够支撑自身的未来的渐进转型。
Q:可以说,长三角的产业要比珠三角产业发育更为成熟。
袁牧:是的。长三角的区域发展拥有十分多元的支撑力量,包括国企、浙江民营企业、江苏省过去大量的科技人才力量等,这几股力量结合起来就面临企业的多元化整合,包括制度管理方式、投资、金融以及产业的多元化组合,这种组合足以让它应对突如其来的各种暴风骤雨。而珠三角基本上是一种模式,缺乏多元性。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没有第二个模式来应急,就会面临崩溃局面。
Q:能否做一个预测,中国发展未来的20到30年里,最具潜力的或最有可能给人带来惊喜的发展区域在哪里?
袁牧:最有可能给人带来惊喜的发展区域,一定是目前发展不是很发达的区域。未来十年,政策导向为先,对产业导向的把握会影响中国所有的城市,而影响的大小,取决于城市本身的发展程度。另外,一种可见的情况是,一座城市的发展给国家和周边城市带来经济效益,但却没有给自己的市民带来福利。而只有给市民带来幸福感和福利,才是真正值得欣喜的事。
发表评论
最新评论
 投稿
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