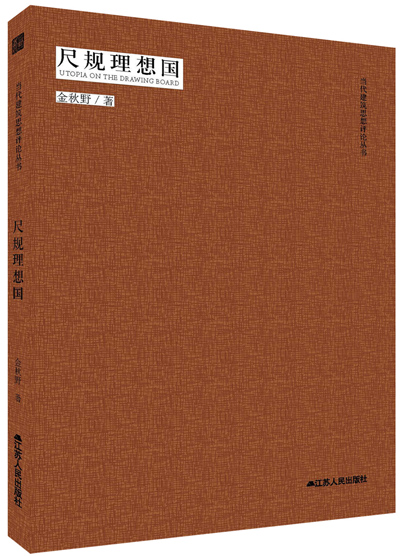“鸟巢”之后的李兴钢
来源:网友Kjoliver1投稿 2016-07-20

著名建筑设计师李兴钢
2008年9月17日夜,残奥会结束,“鸟巢”灯火阑珊,北京的奥运之梦至此告一段落。李兴钢一个人独坐在国家体育场西南包厢的看台上,面对着空无一人的跑道,内心思绪万千。在一篇题为《喧嚣与静谧》的回忆文章中,李兴钢记录此刻的心情道:“只有前所未有的轻松与释然,心里如此沉静。”
从2002年12月竞赛方案启动算起,李兴钢投入“鸟巢”的设计建设任务已近6年。尤其是2003年到2005年,每天都要全负荷地工作,有大量的具体问题要处理,有大量的图纸要完成,由于紧张过度,开始出现睡眠问题。对于建筑师来说,那种压力是史无前例的:一份国家梦想,加上全世界的注视。“鸟巢”是限期施工,也是边设计边施工,前面犯了错误,还要在后面紧急加以弥补,这个压力不是常人所能承受。到工程中后期,方案阶段已经完成,李兴钢和他所代表的设计机构成为法律上的第一负责人,任何一点疏漏都可能很快演变为工地上巨大的失误。未来几十年,这样重大的工程项目也再难重现。
建筑师作为现代社会职业分工的产物,在个人信念和职业价值取向方面往往将自己视为自由的创造者,是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可是李兴钢做这件事,却总让我觉得有一种传统中国士人的情怀,与这个国家的这段历史同进退。我想,汉代的将军远征西域,大捷之后,望着漠漠平川和猎猎旌旗,心中大概也是这样的轻松和沉静吧。在市场化的今天,国家大型建筑设计院已经开始了痛苦的血缘切割过程,可是当初选择在“体制内”从事建筑设计的人,未尝不是一些以传统方式看待个人与集体关系的当代中国人,而所谓的“国营单位”,又何尝不是古来“家国模式”中世族的一种现代变体,看似稳固保守,其实是承担着不小的历史责任的。说它不伦不类也好,说它妨碍了现代化的进程也好,我们都很难不去面对一个现实:当身边的一切都市场化之后,个人与国家之间再也没有制度的缓冲,一份赤裸裸的社会契约,切断了唯有在大家族中才能保有的丰厚感情和人生景致。
有人说建筑师不妨好好做个建筑师,管管建筑自身的事情,能管好就不错了。其实哪儿有什么事情是属于建筑学而不属于人间世界呢?建筑师把建筑太当回事,不再是个天下的人而只是个“建筑人”,这是非常危险的。古人说文章只是余事,读书人当做天下士,志在拨乱开新,建设礼乐,这样的人,文章亦无人能及。时势之下,“鸟巢”显然并不只是建筑学内部的风景,参与其中也就并不只是单纯地做个建筑师该做的事。这是好事。职业分工出来的现代建筑师,他如果没有胆量和眼光往职业以外看,每天只是做做建筑想想建筑,甚至委身于建筑,那其实也很难把建筑的事弄清楚。所以“鸟巢”还真不能只把它当个建筑来衡量,建筑在此也只是“余事”。回想那个时候,与历史同进退也要有人看不顺眼,觉得辜负了现代建筑师的独立人格,这实在是一种“现代的荒谬”。
奥运谢幕之后是“十一”长假,李兴钢让自己彻底放空。然而此时,一种焦虑乘虚而入。这份焦虑,显然是将军没法带兵打仗的饥饿感,手边的工作不能满足内心的需求,他已经无法让自己适应和风细雨的工作状态。于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对项目来者不拒,一个接一个地去处理,好让自己重新进入紧锣密鼓的工程节奏。
这时候,隶属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李兴钢工作室已经成立5年了。这个工作室成立于2003年下半年,与“鸟巢”的设计工作几乎同步。工作室成立之前,李兴钢并不认为有必要凭空多出这样一个机构。但是,随着“鸟巢”设计工作的进行,他的看法变了,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事务所有条不紊的运转模式、高效的工作机制和创造性的成果让他深受触动。李兴钢意识到,单是靠设计院总建筑师的身份去调动人才、根据项目需求随机搭配的工作模式,其实不足以完成自己的设计理想,唯有搭建一个如手使指的个人团队才能达到类似效果。这是由建筑专业特殊的思考模式所决定的——纵有千军万马,也须决策于一人。
在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事务所,工作人员都很有个性,很自我,设计能力也很强。但是,这些精神上卓尔不群的设计师,在事务所里却能完全听命于两位领导,保证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很多人对老板也有种种不满,但在一个体系下,在工作状态里,都能把个人的效率发挥到极致。就这样,在整齐划一的协调步进当中,个人不仅仅是充当一个画图机器,他的创造性也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这样的生产机制,是要靠一定的精神力量来维系的。当李兴钢尝试将这种工作模式引入自己的设计工作室的时候,却发现并不是那么容易。
1998年,李兴钢获得了一次出国进修的机会,有三个月的时间到法国建筑师事务所里去参与实际项目。他没有浪费这次机会,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观察和学习。他独自进入项目组,白天跟法国建筑师一起讨论绘图,下班乘坐地铁,按图索骥,把一本巴黎现代建筑指南中的项目看了个遍。多年以后,李兴钢提起这次游学的经历还是倍感亲切,他很珍惜那种彻底融入欧洲社会生产过程的切肤体验——沉浸在巴黎这个国际化都市特有的文化氛围中。20世纪末,中国还没有迎来国际建筑师的大举入境,多数本土建筑师对西方建筑行业仍然停留在想象阶段。李兴钢去国怀乡,一直都在工作中行走,在行走中思考,在思考中工作。在他心中,真正让人困扰的问题是中国在现代世界中的地位和处境,而这与一位建筑师的职业又是息息相关的。建筑师并不仅仅代表一位富于创造力的自由个体在发言,在世界眼里,一个人注定无法摆脱自己的精神血缘和文化身份。
这份问题意识,在他发表于同一时期的文章中非常清晰。那时候他经常提到日本,对日本和中国之间对现代文明的应对策略加以比较。2002年,他在一次访谈中说:“中国建筑要走上世界的舞台,必须有两样东西,一是要在现代化方面和国际接轨,二是一定要有中国自己的东西”。因为有这样一个自觉的文化意识,李兴钢在欧洲看到的,其实是发达现代人居环境中中国现实的倒影。城市给他留下的印象比建筑深刻,现代生活的组织方式及其背后的运行机制,要比个别建筑的设计美学更能引起他的思索。李兴钢利用周末只身来到罗马,在凯旋大道两侧的古罗马遗迹中留连徘徊,那些大尺度的残垣断壁,以及为了加固或方便行走而修筑的围栏和步道,共同组成了一个令人震撼的现代空间,几千年前的人类遗物如此令人动容。李兴钢不禁追想路易斯·康当年在同一片废墟中游历时的情感思绪。在法国的圣米歇尔山,李兴钢看到的也是一个有着三维空间层次的立体宗教综合体城市,并觉察到这座孤岛的空间结构对鲍赞巴克的影响。李兴钢思考的是欧洲古代城市的结构性组织对当代生活和当代建筑制度的作用:何以在这样一片古老的土地上生出了现代设计语言,以及使用这种现代语言的欧洲建筑师如何对待他们的往昔。
李兴钢说:“欧洲跟中国面临的相似问题是如何在一个有着悠久文化的土地上进行现代化的城市建设,这是一个有意义的观察,意义在于,欧洲人也有如此深厚的历史传统,但他们何以能够摆脱沉重的文化包袱,轻装上阵。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如此纠结。我们应该向欧洲建筑师学习。再有,我们当代的城市永远不要设想有像古典城市一样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因为城市运行机制已经完全不同。在现代社会机制下,建筑师各自为政,再没有统一权力去控制城市的形态,这种条件下,新的现代城市呈现出来的外界面,亦即城市自身的内界面注定是混乱的,因为每个建筑都想跟别人不一样。”
带着这样的认识和体验,李兴钢接受了总院布置的任务,加入到国家体育场的竞赛及后续的设计工作中。也正是带着这样的视野和关怀,李兴钢以一种平视西方同侪的立场,开始搭建自己的工作室,一个从“现代”眼光看来相当奇特、介于体制和个人之间、介于历史和现实之间的独特设计机构。而这个机构,其实承载着李兴钢个人的认知和经验、谦逊与抱负,因而也充满了可塑性。
在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事务所的工作经历,让李兴钢深受触动。即便以西方世界的眼光来看,这家事务所也是非常独特的。一开始,李兴钢感受到的是审视和排斥,他们对外人并不特别友好,不许拍照,要签署保密协议。但在工作之余看到他们的大量作品,内心深为感佩。大量方案,已实施和未实施的,都保持着相当高的设计品质,材料安排和空间设计俱臻上乘,让人惊诧。李兴钢留意的并不是这些具体的设计案例,而是一个事务所的工作状态,这与国内完全不同。对他们来说,设计不是一个灵机一动的过程,而是在种种线索的铺陈、大量信息的筛选过程中成形。日常工作都是团队合作,主创建筑师只是最大的决策者,他的直觉和感性部分充当了思维发动机的角色。他们也非常重视艺术家在团队中的特殊作用。这些工作方式、工作态度和设计思路上的冲击,在后来李兴钢工作室的发展完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李兴钢开始认真琢磨这种“研究式”的建筑生产模式的具体细节。
在李兴钢工作室,一个设计项目启动之后,大家不是各行其是,而是遵循设定目标——分派任务——集中讨论——目标深入的模式循环往复。比如第一个阶段的研究要分头安排,汇总后召开第一次讨论会。会上,每个人谈自己的认识和思路,有人从基地环境角度,有人从功能角度,有人从历史文化角度,等等。这个时候李兴钢会进行主导,确定下一步发展的方向,选出一种或几种可能,然后再次分工。项目就按照这样的方向持续进行,不是各自为战,而是为同一个目标来共同工作。
但在这个过程中,问题出现了。尽管采用了类似于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事务所的生产机制,李兴钢发现自己工作室里的设计师们很难保持与前者类似的整齐划一的协调节奏。换句话说,那种特殊的精神力量所带来的高度凝聚力,并不是朝夕之间可以养成的。这种区别,很大程度上源自文化差异。在欧洲的学校教育中,例如ETH,本科高年级的设计教学其实已经非常职业化,但同时又能保证思维的锐度和强度。这一点与中国建筑教育中的所谓“职业化”概念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年轻建筑师往往表现得相当成熟,却也保留着观念上的冲击力。而中国的年轻设计师却保持着学校教育的异想天开,或过早进入毫无理想的重复操作。李兴钢认识到,真正的实践必须具备学术性,但学术性不等于学生气,学生气往往是因为学院教育思维僵化、脱离现实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作室就像是学校教育的延伸,只是转变了方式,开始沿着一条现实的实践之路继续思考、探索、钻研。对初涉工程领域的年轻人来说,这一转变有着特殊的意义。设计如果离开了研究,就无法保证思考的锐度和质量;如果离开了实践和社会,则很容易陷入专业性的自言自语。所以李兴钢会同工作室里的年轻人说:“我们是半学校半社会的状态,并不是完全的社会生产状态,也不是完全的学校状态。”
在李兴钢心中,建筑师工作室的理想状态介于学校和社会之间,它的思维强度类似于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学校,但接触面却已是真实的社会。这里有密切的交流和争论,也有紧张的合作与愉快的旅行,一切都笼罩在积极稳健的研究气氛中。乐观地说,这种工作室得以分享大型设计机构的项目资源和技术力量,同时保持着小规模理想主义事务所的紧凑高效。但凡事都有两面。工作室的项目数量众多且类型丰富,设计师对项目的设计品质要求均一,也不容易将注意力集中在个别富于创造潜力的任务当中。而这恰恰也是李兴钢工作室这一类特殊形态的中国建筑事务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为此,李兴钢兼收并蓄,在保持传统大院的工作习惯、取法于域外事务所的组织方式的同时,努力开拓着属于中国当代的个人化建筑设计工作模式。各种观念和思路从生涩到圆润,逐渐融入“鸟巢”之后的十多个建筑设计任务中。对于一个至今只有16人的小型设计工作室来说,他们的项目数量是非常惊人的,这些项目中有13万平方米的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也有小巧别致的威尼斯双年展纸砖房;有3座博物馆,也有西柏坡希望小镇、唐山“第三空间”这样的住宅项目。这些项目都包含着设计师的巧思,建造质量多属上乘。在长长一串作品名单之后,是这个成长中的团队的心血和乐观积极的精神。
以2008和“鸟巢”为界,李兴钢将自己十年来的工作分为前后两个五年。前五年的作品如“复兴路乙59-1号改造工程”,探索立体园林和空间化的视觉处理,仍然受到赫尔佐格与德梅隆作品的不少影响。从2003年11月工作室集体的苏州园林探访开始,李兴钢对中国古典园林发生了真正的兴趣。到2008年前后,像“建川文革镜鉴博物馆”和“威海Hiland·名座”等作品开始出现对园林空间语言的探索。这个趋势在后五年的设计中已经发展成常态。为了统一思想、强化精神凝聚力、改善工作效率,李兴钢提出了“几何与胜景”的概念,它既是方法也是目标,在近期的设计项目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李兴钢放下了“鸟巢”带来的喧嚣、荣誉、忙碌和疲惫,甚至不去回味,重新走上那条属于自己的探索之路。这条路,其实就是李兴钢本人对中国问题的一如既往的关注,可以说,这已经成为他职业生涯的特殊色彩。李兴钢不止一次谈到大学时代登上景山,俯瞰紫禁城那一片光芒耀眼的屋顶,心里升起的对传统文化的认同。谈到传统文化在20世纪的断裂所引起的切肤之痛,在一切向国际接轨的年代,身边像李兴钢一样有着深沉感受的人并不在多数。如何弥补这一文化上的裂痕,使自己不再充当一个现代世界中的流浪者、失语者,自中国建筑起步阶段就成为人们内心的期盼,但对当下的本土设计师而言,依然是茫无头绪。看李兴钢的工作,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能体会到那些俊逸温和的形体语言背后深藏的对传统的向往和追求,这正是当代中国建筑领域难得的发自内心的大愿力。回顾十年来一系列或大或小的设计作品,里面包含着一份罕见的诚恳与郑重,转型期太多夸张和麻木看也看不完,所以一份郑重的交代总是值得珍惜的。
作者:金秋野,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设计基础教学部主任
发表评论
最新评论
 投稿
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