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7 Archsalon——当代中国青年建筑师主题沙龙”成功举办
来源:畅言网 2014-08-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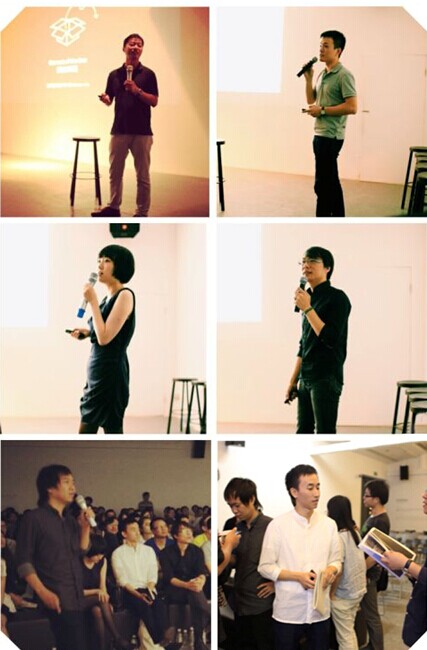
M7 Archsalon对谈录Ⅰ:设计理想之乌托邦与现实
朱渊:在这个非常特殊的场合,我今天安静地坐在下面欣赏并学习了各位小有成就建筑师做的作品,心中非常感叹。所谓艺术来源生活,建筑更需要来源生活,更需要与人发生各种关系。我觉得各位建筑师在介绍自己作品的同时,无不散发作品与人之间的这种纠缠及挣扎。同时我也感受到,各位建筑师在人与法则之间的这种较量关系。
大家在刚才看到的非常精妙图片,以及非常具有唯美效果的一些照片时,也许能够感受到,它们背后会有很多的矛盾、很多的纠结,很多非小清新状态背后的故事。所以我特别想听到,可能也是在座有些人很想听到:当建成一个好的作品,或者向甲方推销一个概念的时候,难道真能马上得到甲方认可,并接受所谓乌托邦式的理想吗?实现过程是否一帆风顺?非常希望能够听到各位建筑师分享背后的故事。
孔锐:一个项目的推进和实施,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戏剧性。朱老师刚才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工作,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在讨论与人的关系问题。所以,一个漂亮的房子,或者一个很好的设计,往往都是很后来的事情。之前大量的工作是与业主,与方方面面的资源和力量做沟通和协调。当你认真地去了解业主的想法和目的,当你仔细地去分析项目面临的限制条件,这些才是一段美妙工作的开始。我想,对于美好事物的追求,所有人都是相通或相近的,所以当你从他的立场、处境、角度与帮他梳理他所面临困难、压力、局限后,再用我们的专业能力给他一个解答,一个好的结果就会变得自然而然了。
葛文俊:在设计初期,我们一定是站在最终使用者的立场上,或者说是投资的立场上。做出来的东西必须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态度,但是我们做事情这个过程带有极强的批判性。我们故意放大某一些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业主非常认可,可能有点偏激的方式来强调这方面的价值观,用一种戏剧性的办法把它给实现出来,最终实现的东西,它的关注价值观一定是触动业主的神经。但是实现过程最终呈现出来的东西,因为我们采用偏激的状态,我觉得达到一种不平常的状态。
朱渊:因为有可能你要推销设计师心中的美好理想,却用另外一种方式推销给甲方,甲方认可的东西同时是你心中另外一块需要实现的理想。你面临不同的人,同样的理念可能实现是不同的目标。
葛文俊:比如说南通规划展览馆模仿荷叶,甲方一开始给我提出这个难题,我觉得比较土,但仔细一想,这种具像的审美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非常大的特色。比如你到黄山去,所有的特色大家能够记住它,多是因为它的名字和象形的东西。这是我们祖先一种特殊的认知方式。既然是我们的传统,我们就不应该去排斥。我们应该选取一种方式,做出一种诗意和神韵,给人家一种空间自由的感受,这个是我们要做的。最终也是通过一些研究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有5轮到6轮的方案,得到还比较认可的一种象形方式。对于一些业主的需求,我态度上是非常拥抱的,但是我的方法一定是很特殊。
朱渊:从我们设计来说,设计好东西需要很长时间,你需要思考。当然可能在当今中国,你不会有太长时间,你怎么样去平衡设计质量跟快速节奏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快与慢的节奏的之间,又怎么样去平衡事业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沈禾:这个问题我想首先请徐晋巍来回答——4年100个项目!
徐晋巍:其实这个问题我也经常自己问自己。早期基本上是完全依靠个人能力在做事,是蛮工作狂的。慢慢的,尝试把自己的这种工作方式,变成一个简单的套路,以一种能让团队容易接受的方式,形成整个团队的一种工作模式。我们团队在过去的两三年中,把我个人习惯的工作方式,通过训练,慢慢得学会或者继承,更多的应该是相互之间的融合。所以我们为什么没有选择尝试做一些(造型上)非常怪的项目,而是更多的选择用比较理性的,有规律的方式,做一些能够被大众所接受,大部分人看了都觉得还不错的项目。我们试图用一种不变的法则,去应对所有变化的项目,让自己理想中的工作状态,能够变成整个团队的一种工作方法。
相南:很遗憾,我回国的第一年是没有生活的,90%的时间是在工作室度过。创业初期这个就是现实,我们必须接受,能做的就是尽力而为,因为这是国内的一个现象。这些现象集中在整体社会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对于时效性的追求,短时间这个事情无法改变,因为大环境在这个地方。其实现在工作时间方面已经好多了。
沈禾:我没有觉得好,一星期要飞三次。那么到底是自由还是不自由?
相南:我们向往自由,这是一个目标。有些事无法改变,所以只能尽我们所能做得更好。我有想到一些方式:第一我认为团队的效率最重要,一个高效率的团队能使你节省成倍的时间。第二就是高效的团队管理,包括对人员的管理、技术的管理、建造图纸的一些方式,这些可以使你在有限时间里面,调动你团队里面更多人力资源去完成一些事情。同时还有对团队进行培训,我们的培训周期很长。
沈禾:这个是不是得益于你之前在国外较成熟的事务所养成的一些习惯?
相南:因为在国外人力资源非常贵,怎么让人在有限时间发挥更大的效率,这方面是我们可以提高的。我把这些东西搬过来以后,可以使团队工作效率成倍提高。但代价就是整个培训周期非常长,需要每个人都熟悉这套系统,然后愿意接受这套系统。
M7 Archsalon对谈录Ⅱ:设计思维之历史与未来
沈旸:我的第一个问题,历史作为一种思维,或者一种设计思维,你们是怎么去看待历史的?第二个问题,如果10年之后,经验已经很足了,让大家做事务所,或者回学校教书,你们愿意做哪一个?
葛文俊:我对历史特别喜欢,尤其喜欢古代的艺术,包括家具一些东西。比如明式的家具,如果你仔细体会,它比现在当代宜家有太多的现代性。我们有太好的传统,我们可能是忘记它了。你会发现我们的古人用经验主义发扬了上千年的手艺,这种文化和审美是非常非常有生命力的。我们这一批人特别有生命感,要把它带回来。
孙乐:说到历史跟设计的关系,我认为更根本在于人的行为。拥有相同历史传承的人的行为会影响你对传统的理解和思考,最终影响到你的设计如何去做。比如对石库门的理解,只是把石库门形象照猫画虎那个不是历史传承,而真正的历史是它的空间肌理给人带来的影响和行为记忆。它可以承载更多人的行为活动,开放的、私密的,对应的是“主弄”“支弄”不同的空间形态,这是跟设计更贴切的东西。
关于10年后的问题,我没有想过。如果10年内不开事务所,10年之后应该不会开了。也许在10年里面不知道发生什么,突然想回到学校里面,去分享,或者是想走到校园里去做些什么,现在说不准。
孔锐:对我们而言,历史有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层面,它帮助我们寻找语境并树立信心。我们去看历史,或者具体到建筑史,会看到一个文化的源流和它的潮起潮落。比如唐和辽代的建筑,从佛光寺、独乐寺到奉国寺到,从建筑、雕塑到绘画,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发展和演进的脉络,里面有文艺复兴,也有巴洛克,甚至“现代性”,那些都实实在在发生过,并且依然伫立着。这种跨越千年时间维度对建筑师而言是十分宝贵的,因为我们可以从中检视自己工作的位置和意义。第二个层面是责任感。我们今天的所做所为,或近或远,终有一天都会成为历史,所以当下就是历史。因此我们需要认真审慎地对待工作并思考问题。
范蓓蕾:关于10年后愿不愿意去做老师教书,我们肯定非常愿意。在我自己的求学过程中,来学院任教的实践建筑师给我影响很大。在学校里,可能更多是培养一种素养,一种基本的理解建筑的能力,但是对于整个世界的多样性、生活的丰富性是无从获知的。但那些建筑师老师来了之后,他们拓展了你的视野,你会慢慢知道自己生活的方向或者态度。
历史就是过去的生活,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挺可怜的,因为交通方式和信息传播的爆炸式发展,使得我们的距离感和时间感变得很薄弱。比如我们现在三个小时就能飞到的地方,古人坐船可能要三个月才会到达。在那个过程中,他们对于时空的感知,对于生活的体验,对于世界的印象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强度。我是很羡慕古人的。今天虽然我们生活的世界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把过去的一些体验和情感的东西留下来一点,这也是我们关于历史这个问题最大的一个感触吧。
徐晋巍:其实在自己的事务所也一样可以当老师,当老师不一定在学校里,在生活里也可以。当老师是一种状态,把你自己的东西分享给愿意学习的人,把你的经验让别人学习,或者传承。在事务所里可以跟年轻的建筑师交流经验,这个是我理想中的教学方式,这种教学方式跟古人相似,它类似于师傅教徒弟的方式。当然,如果10年后,有机会可以回学校当老师的话,我还是很愿意的。
历史太遥远没有办法真实的去接触,能够接触的可能只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我做的很多设计,更多的不是从遥远的历史中去寻找灵感,更多的是一些儿时记忆。有时候回到浙江老家,也算是古镇,但发现小时候的记忆完全不存在了,一些在我看来是非常美好的城市记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更想做的其实是能够把儿时的一些记忆、一些空间能够融入到现在的设计中去。
沈旸:我们70后这一代人,可能没有出生在一个有回忆有历史的氛围里面,包括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各位的回答启发现在人找寻历史和回忆的方式,让我们感到原来有那么多有意思的东西,还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去学习它,所以我觉得既很痛苦,又很欣慰。
葛文俊:人如果有追求,那一定是不太容易能得到,但是又能够追求到,那种状态是最好的。如果是我们身边从小就有的东西,对这些东西的感情就会留下。
相南:历史毋庸置疑,对于建筑师的经验积累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每个人都不会否认。我们当时做中国美术馆项目时,和一个华人馆长做密切交流,他对中国历史非常了解,特别是敦煌,后来这些历史被非常象形地还原到中国美术馆里。即使是西方思维,他们对中国历史的尊重远远超出一些中国人对中国历史的尊重。
关于教书,我从毕业开始到工作,还没有想过。因为对我来说,精力有限,我想把100%的时间投入到我的工作室里面,投入到我的设计里面。还有一个原因,不过我没有细想过:建筑教育是在学院里面,还是工作里面?我认为我70%—80%是在工作当中形成的。不过我在这个岗位通过一些间接的方式也可以做到教书育人。
沈禾:总结一下,第一点是历史,各位其实在历史当中寻找了很多素材,这些素材其实构成了建筑师将隐藏在心中小小的建筑理想卖给业主的一个钥匙。这是他们自己强的东西,他们要研究这个东西。第二个是学院教育和建筑师成长关系的问题。其实不管是我们要去学校教书还是在工作室里培训,其实都脱离不开我们建筑师作为最初的手工业者,一种师徒之间传承式关系的状态。谢谢各位精彩的对谈。
发表评论
最新评论

 投稿
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