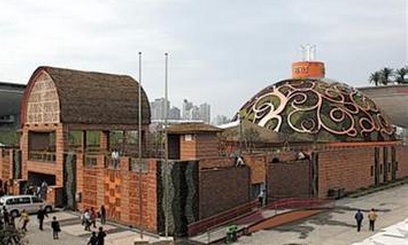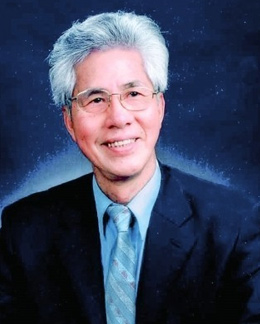如何让建筑承载文化,其要害就在设计创意的确立和表达上,问题的反复出现,都与我们在后现代大文化环境的气场中,否定建筑学科的核心元理论直接相关……

这是位于北京市正南大兴区被称作“龙凤呈祥”的“地标式”建筑群。媒体上的文字介绍是:“18号、28号地块的落成,为大兴城市天际线增添了优美的弧度。”又称“龙凤呈祥的意象也昭示着大兴经济与文化的腾飞与繁荣。” 但明白人怎么也看不明白:把一字形排开的建筑,生硬地拼凑成“龙头、龙身和龙尾”,怎么就和“优美”联系起来了?图面左侧双曲面造型隐喻为“凤”的北京兴创大厦,也因比例严重失调、扭抳造作,而在畅言网2013年全国十大丑陋建筑评选中名列第二……
文化概念,是知识库中用得最为广泛,也很容易被乱用的概念之一。国内词典称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这里,我们暂且不涉及人类整合文化学同构中三个不同文化层面的分类概念,而只简明地将建筑所承载的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不难理解,我们常常讲的“设计创意”,其实,就是我们在建筑的物质文化及其精神文化方面所寻求的“设计意图”,也即我们要往建筑上“加载” 的“文化法码”。
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都亲身感受到了,建筑变得越来越麻烦,而麻烦建筑也变得越来越多了。这是为什么?我在重温《后现代的生存》这本书的经典要义时,才开始认识到,上面说的“两个麻烦”的建筑现象的产生,不仅是必然的,而且还会长期存在下去。1999年我曾读过这本书,尽管在书上画了不少记号,但却感受不深。当我再一次在书中重点处反复细读,和对照设计环境的现实时,才如梦初醒,真正体察到了书中说的那个意思:“后现代”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或“主义”,更是“一种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而这种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却很难让我们去廓清,正如书中深入分析的那样,既不能用“相对主义”来解释,也不能以“虚无主义”去看待。但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这种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无视,甚至否定各门学科中不需要证明的“元理论”,即“一切理论上的‘规律’、‘真理’或者‘定义’之类……”正因为如此,进入后现代历史时期始终困扰着我们的后现代主义,“不仅是一种文艺现象,甚至也不仅是一种社会文化思潮,而且更是一种新的方法论、新的世界观,是一种以现代科学为基础,又反过来对抗现代科学的世界观、宇宙观和人生观。”这样一些深刻的剖析和揭示,让我终于甩掉了被各种表面现象所迷惑的一头雾水。原来,包括我们埋怨不休的“被设计”在内的“建筑麻烦”,和非要强行占领“建筑形象高地”之类的“麻烦建筑”,恰恰都是后现代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下大文化环境气场中的客观存在,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使得这种客观存在所展现的矛盾更为突出、问题也更加严重,甚至可以这样说:即使我们翘首以待的《建筑师法》颁布了,也不能指望把裹夹在后现代大文化环境气场中的负面建筑观念和建筑意识,都统统关进笼子里。无疑,这种客观存在的必然性和长期性,会迫使我们走出个人理想主义的“象牙之塔”,并在必须面对的“两个麻烦”的设计环境中,增长智慧,赢得生机!
在重温《后现代的生存》时,我也注意到了美国学者D·格里芬从不同文化领域的具体分析着眼,提出了“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和“破坏性的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概念。这种观点,也确实能说明后现代中国建筑创作的实际情态:多元、共生、包容,以及人性化走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新气象,不能不说是与后现代文化观念的滋养分不开的;而与此同时,当代建筑的乱象,也受到了“破坏性的后现代主义” 的牵连, 特别是在“如何让建筑承载文化”的这个要害问题上,其负面影响是决不可低估的。无论是抹杀建筑载体中物质文化在其功能、技术和经济诸方面的规定性也好,还是一厢情愿地把建筑载体中精神文化当作可以任人臆造和表现的东西也罢,这些都是否定建筑学科核心元理论——“适用、经济、美观三个建筑基本要素相互制约而又融于一体”的基本原理的集中表现。这也正是作为文化载体的建筑,之所以会被文化严重扭曲的根由所在。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适用、经济、美观”各自概念的内涵已有跨跃式的深化和拓展,但不论怎样,“适用、经济、美观三位一体” 的建筑观,仍具有无法颠覆的普世价值意义。
建筑,之所以不同于其它各门类艺术——同样作为“文化载体”的雕塑、绘画、音乐、文学、电影、戏剧等,就是因为它具有建筑学科核心元理论所阐述的“质的规定性”。因而不难理解,建筑承载文化不离谱,并不只是在“形式美”上不出“幺蛾子” 就行了。事实上,比起其它各门类艺术来,建筑在承载文化时,确实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不论是建筑所承载的物质文化也好,还是精神文化也好,都要遵循建筑创作的基本规律,融合于建筑的生活美、艺术美与形式美所构成的“建筑的整体美”之中。我们很容易只从建筑的外观上去进行评议,其实,在“乎悠人”的外观掩饰下,同样是不靠谱的建筑,更具有“为拼形象而挥霍资源” 的倾向性和危害性。这里,有必要再一次指出,总建筑面积指标的框定,往往不能控制建筑空间的巨大浪费,而即使是在总投资的范围内,建成后工程常年能源消耗和总体运营成本居高不下,早已是屡见不鲜的事实。所以,建筑所承载的物质文化的真实品质究竟怎样?这对以“大手笔”设计见长的大腕来说,是很容易忽视的一面,要说有人“不屑一顾”也不为过。我确实有一种“时过境迁”的感觉,现在很少能听到和见到建筑名家像程泰宁先生那样发出的心声:“技术经济的合理性,永远是衡量建筑作品内在品质的不可分割的一个要素。” 自然,这种“合理性”的内涵,也应包含技术经济的“实效性”和“长效性”。
面对后现代大文化设计环境,要有两手准备:把握机遇,实现确有先进理念和优秀创意的方案;有麻烦纠缠,则以设计意图不离谱为底线,确保作品不失品格……
如前所述,处于改革开放和后现代大文化环境气场中的建筑师们,要想应对“建筑的麻烦” 和“麻烦的建筑” 的挑战,就得走出个人理想主义的“象牙之塔”。实际上,设计赋予建筑师的社会责任感,也会让我们想到这样一点:在设计中,如果一遇到来自瞎指挥或插横杠的馊主意、歪点子,就抵触,就懒得“侍候”的话,那很可能就失去了一次堵塞“不靠谱设计” 的重要机会。为什么我们不主动去占领设计阵地,反而要后退呢?!让社会上尽量少出现一些“憋脚建筑”或“丑陋建筑”不好吗?!
发表评论
最新评论

 投稿
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