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力:
我们那里有这样的标准,尤其是使用的铺地和小品建构物。澳大利亚和美国很相似,之所以走在生态设计的前列,是因为考虑到了材料是否可再生,几十年后材料是否可再度利用,以及是否有辐射。比如上海黄浦江边的殖民建筑使用了大青石,而由于放射性因素,澳洲禁用一部分岩石,首先要求景观材料不得危害人的健康,其次也考虑材料对环境的影响。现在普遍使用花岗岩石材,而我个人很推崇可渗透性材料,不仅造价便宜,也能解决地面排水问题。我认为评判材料是否生态的标准,首先是它对人体是否有害,第二是从长期使用角度,对环境是否有不利影响。
蒙小英:
这可能涉及到了可持续性,就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范围内,材料是否能被多次回收利用?英国最近造了一艘特殊的船,材料全是塑料瓶,这种瓶可以被再利用。现在生态的概念可能已经不是一次利用,涉及到了多次的重复利用。
耿佳丽:
刚才听大家谈生态,发现我们说的“生态”多带着褒义的意思,其实我觉着生态应当是个中性词。我们经过了低水平的发展阶段,现在大家渐渐重视生态这方面的考虑了。刚才大家提到的生态评判标准,我们土人在景观实践过程也在尝试着去整理和制定,但目前并没有如同建筑的三星认证标准那样的评价系统。我们主要是基于景观生态学,从廊道、斑块等角度出发,通过查阅数据和相关资料,去构建生态安全格局以指导设计。至于生态评判标准,还有待大家进一步的实践。我们在项目设计中会参考国外一些标准,根据方案的实际情况和甲方意见做出一些调整。
蒙小英:
作为设计师,我们究竟为谁设计?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后来,我们探讨了很多,发现很多东西需要归结到政策或政府层面。许多国学大师都认为中国是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西方国家可能更强调集体或个人,因此更容易推行“公众参与”等理念。我个人对北欧的景观比较感兴趣,他们的设计师坚信设计就是为大众服务的,景观项目设计不仅在功能上满足实际使用,而且还考虑引导大众的审美。另外,设计师也会自觉地去发现一些社会问题,通过设计去改良和改善问题,从40年代的景观设计师到现在新一代的设计师一直是这样的。所以虽然个人的力量是很微薄的,我希望通过我们的景观设计,不管是园林还是景观能够提升大众审美。开始我不理解丹麦大多数景观项目的设计师里都会有景观设计师、艺术家、建筑师,后来知道丹麦要求一个项目投资的百分之五需要拿来做公众艺术这个规定,就明白了。这种政策导向非常有利于建设高品质的环境,也能通过环境的改善和建造来提升大众审美。
我个人倒是希望中国今后的园林能更多体现我们地域景观的一种创造,这种地域景观其实也相当于我们的传统园林怎么发扬。另外就是我们的农业景观也是地域景观创作的源泉,俞老师在推行,我比较认同他用的那种玻璃钢的红色,中国红的东西还很有特色。北欧的景观设计师会把农业景观的东西提炼成景观的设计词汇,成为园林设计中非常富有地域特色的设计语言。我现在正在尝试这方面的研究。刚才郑总也在讲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模仿西方,其实每个国家都有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也许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太快,在模仿和学习外来的东西时使我们出现了消化不良。像某些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消化得很好,创造出自己的东西,园林发展自然就会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是我的一点感受。

活动现场
张力:
我比较认可,欧洲景观设计的方向的确与澳大利亚、加拿大不同,包括美国,因为这三个国家建国时间比较短,在文化层面上可能没有欧洲深远。中国设计师为什么认可欧洲?文化沉淀时间会比较厚一些,文化内容含量不一样,层面的厚度可能差不多。我们那边注重生态的多一些,欧洲的艺术涵盖性会高一些,比较明显。比如丹麦是要求一个项目的百分之五需要拿来做公众艺术,刚开始我不理解他的每个项目都会有景观设计师、艺术家、建筑师,可能跟政策导向有关系。
蒙小英:
跨专业的合作是我们近年项目设计中比较注重推行的,就像我们刚才提的第二话题铺装,现在的铺装成分可能少了一些艺术。铺装是技术与艺术统一中比较容易实施的部分。前期有艺术家介入的话,铺装图案的设计就会变得不同。现在是景观设计师包揽了铺装设计所有东西,其实我觉得还是术业有专攻的,尽管你的色彩感觉很优秀但还是不如专业的,这是我与不同专业人员合作的体会。现在不管是建筑还是景观,我们都会跟艺术家去合作,是一种尝试。这样不能说设计的东西很完美,但是至少能使功能与视觉尽可能双赢。
张力:
不能说艺术家的东西就可能完全实现,艺术家提出来我们那边区政府就会有一个比较重点的讨论。比如意大利的艺术家来设计墨尔本的艺术馆,那是国家艺术馆,当地的市政府是否能够通过或者认可设计方案,他有自己要求在技术层面上是否能够实现,前期会跟艺术家合作,但方案中期的时候就会与规划等一个专业团队合作。景观设计师全程涵盖与不同的专业人合作,能够把精美的作品呈现出来,这是比较难的。刚才蒙总提到政府有个百分之五的要求,说实在的这就看政府控制的能力所在。因为我在国外做住宅区要报批的话,在哪个区是属于哪个等级的居住区规划的范围,比方说一级、二级、三级,一级对园林绿化的面积是有强硬规定的,达不到要求的百分比就不能做,而且政府总是让修改,上面提到的硬地铺装会有很大辐射,为什么一定要做绿化空间草地、灌木,政府就鼓励设计师做。居住的自然环境给人体的自然感受,国外就把这方面整个细化,政府的掌控是硬性的,达不到一个社区的活动空间就不能通过。买了地要建成什么样,想把建筑用地最大化这是不可能的,要照顾周围的环境,整体的使用功能。比方说建五十多层,就必须要留出多少的公共场地,公共场地里百分之多少是绿色空间,国内在这方面也有相应的要求。
郑越:
国内这方面要看是什么类型的项目,以前园林局与绿化局还没合并的时候,他会掌控所有的方案,任何一条简单的道路方案也要拿到园林去审,居住区的东西也要去审。当时的问题是中央单位我们控制不住,不归北京市管辖,现在的问题是私企老板控制不住,私企老板觉得我有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如果有困难的话我去协调。当初园林局审方案的时候要设计师说的非常详细,现在非常简化,容易加进人的行为意识,所以现在审核时政府只审绿地指标,里面的东西都不需要,除了路就是绿地、停车位就够了,这样就是完全的规则吗?方案就有可执行性了,不会为了加个亭子而纠结,只要绿地指标符合标准就可以了。现在市场开放了,从业人员也比较多,出现很多不规范的东西,由于缺乏经验存在很多问题,如果没有政府的把关、公司内部没有审核最后建成什么样出来后大家可想而知。我觉得每个公司都有过这样的项目,因为设计师都是从不成熟到成熟的,但是由于政府缺失,每年园林有针对施工的检查,优秀的设计评比,大家都会跟政府说是不是找个规避的方案,政策已经是这样子,政府已经发生变化已经无法实现了,只能给控制指标。所以就依靠各公司的老总把关,给政府和大家合格的产品。
畅言网编辑:
某些作品一味追求奢侈、高价格,这是不是一个好的景观设计?
张力:
在中国受投资方的影响的太多,设计师都不自觉的向着这个方向去思维、去做设计,所以这是一个很难改变的现状。可能设计师听到也是比较郁闷的,要听甲方的、要满足政府的要求,又纠结使用者是不是真的满意。其设计师也是戴着枷锁在做设计,在做不想做的事情。甲方要把做的东西卖出去,设计师有的时候是不想做代理,但是没有办法。
郑越:
这个我也有看法,高价格按常理说肯定是好的,然后设计师知道这是高价的,他不知道还有一些便宜的产品也很好。比如刚才我提到的那个菠萝壳,价钱上万元,其实还有便宜很多的,效果是一样的而且还更结实。有的设计师不了解,所以为了保险设计师还是选贵的,体现水平和认知能力。现在设计师很少出来看,包括前期看现场、后期看自己作品的效果,大家的机会都不多,所以设计师自我修养需要提高。要知道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用什么样的材料,在我看来根本没有那么多问题,设计师要知道用合适的方法、手段什么问题都能够解决,解决不了就需要花钱,花钱多了肯定能解决的。但是你不知道有好的东西能让你解决问题,但是便宜的东西在造价允许的情况下是能够解决的,核算不够花钱,设计师不在景观的部分花钱,就在建筑上花钱。如果是甲方什么都不想干,把责任都推到设计师这边,设计师再不会解释,这个帽子就扣在自己身上了。所以说设计师还是要增长知识、增长见识,要有经验来告诉甲方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用的。
余为群:
什么是生态?其实关于生态我的观点有两种,自然型的环境生态和人居的形态。我们一般评估的是人居形态,有人类适合的气温,这有些像经济学中个体经济与总体经济的关系,个体经济比较容易评估,人居生态在小范围的城市、乡镇、住宅中,所谓的人居的生态环境我们很容易匹配出来,可是大的生态环境是个体系,那个体系设计师还要做,也不知道明确的答案。因为那是个非常庞大的体系,今天我们讨论的还是人居环境,所以我们讲人居生态还是要强调是景观设计师要有自己对人居环境的一个判断,要有自信而且要有自己对环境的观点,要进一步去影响建筑师。实际上提到房地产这个事情,关于地产的建筑已经没有太多突破了,就是那几种户型,我要讲情境设计的原因就是情境设计建筑占一部分,很重要一部分是景观,整体性才是情境。在房地产绿化中建筑变成一种背景,设计师要想真正表现根据不同的季节行为去展现景观,而且是有生命力的一种场景的话,那还是依靠景观,所以景观设计师要有自信,景观要去把建筑缝合在大地上。
郑越:
余总说的非常对,我们当初设计望京西园的大平台时也是建筑与景观分开的,一个公司做建筑方案,我们这边做景观方案,然后结合起来一块做,最后才进行建筑设计。在方案确定之后我们要种植大株树苗的地方,我们留的树坑是两米七深,直接就把大树移栽过来。但是我们规划的儿童游戏区的就要把泵房放在那里,覆土只有十五公分,所以只能植草了。还有些协调不了的问题,比如入口的广场区,必须要一个广场来分流,人有不同的活动空间,我们就采取了景观的做法把局部提高。整个广场全是空的,树坑一个个挖下去,等于我们设计的树池子,地下打洞然后树根往两边走,然后里面再回填东西,这就是我们系统的配合问题。哪里种大树我们一开始就设定好了,而不像现在的情况。今天这里也有建筑设计师,现在我觉得还是工期的问题,我们做的等于是建筑设计院的试点项目,一开始跟专业的园林设计院、专业的建筑院一起做吗?我们所有设计的都是在方案阶段做好的,都会预留空间,但是现在的模式是除非遇到特别的项目能够做到这些,目前一般的项目都做不到。
张力:
刚才郑总说的问题就是材料,材料就是机会,新参加工作的设计师的包括工作一段时间的设计师,材料应用非常少,我觉得太单一了,应该让设计师扩大自己的材料知识面,对材料各种性能的把握准确了才能用到正确的地方,对的材料用对地方、而且用的很恰当,这样开发商才会满意。我们设计景观各方面都符合要求,不需要非常绚烂,但我觉得要做到适中,这也是工作中要非常注意的,对材料性能的把握,新材料的性能适合哪种空间,对可再生材料的应用有所推动。
郑越:
比如脱水混凝土,这个技术也是从国外引进的,做过测试同样是下雪,石材路面两天才化掉,但是在脱水混凝土的路面一晚上雪就化掉了,下雨的时候在脱水混凝土上行走,鞋、裤子也不会湿。我住的小区原来是石材现在全换成了脱水砖,一些地产商为了品牌形象采用的风格就是石材,哪怕没有钱用质量很低的石材也都不会去用别的东西。甲方已经确定了某些材料是前期的,后期改不了,除非遇到什么问题才能改,而且像有些材料并不是不好,只是用得是否正确。之前觉得石材好,儿童场所也用石材,有台阶儿童摔倒后就会磕到,包括花池的处理都是需要注意的问题。现在大家知道台阶要用塑胶包一下,沙坑里也不用大石头而改用其他软质的材料了,这些做法都是需要慢慢的学习和积累。
我现在就是有个很深刻的感觉,在水源紧张的情况下,设计师应该考虑如何节水?以前北京市水源紧张,饮用水都不够,所以居住区设计严禁做水景,后来大家都觉得做水景很有档次,开发商都要这样做。我见过很多就是做五公分的水,但是用了三十公分的混泥土来做水池子,很多人也都这样做过。实际上可以使用的材料有很多,包括现在硬质、软质的,是可持续性发展的模式,但是设计师会不会用是另外一回事,而且对于超薄、超浅的水池子能不能做也是一个问题。曾经我见过一个项目,设计师做的水深是五十公分,甲方说两个星期换一次水,而且整体全换,这很难控制,而水是流动的,整个水池哗哗流下来,池塘里面有水生植物,不能控制水的污染。但是现在已经做到八十公分,水里面就可以形成自然的水生系统,现在技术也很多,做八十公分的话在北京做到冬天不结冰,鱼和水草能在底下存活,这些都是水的自净系统,夏天晒不透能够保持水自身的自净。所以说很多设计理念是可以通过各个渠道让设计师了解到的,很多习惯性的做法导致的问题随着科技的进步是能够解决的,包括在不同的地域环境下是有变化的。比如在东北地区要考虑冬天抗冻的问题,在海南地区就是另一种考虑,甲方不专业也看不出来就造成资源的浪费,最终景观效果打折扣。水池子不要做得太浅,做水处理土人设计在这方面是一贯有研究的,前段时间北京市一个项目,从整体宏观的来看北京市的改造,对于居住区有屋顶绿化、表面绿化等。包括健康社区有很多指标,软性、硬性的来改善整个社区的环境,因为我们以前提倡居住区的绿化生态,当时生态放到最后考虑,现在生态肯定是要首先考虑,要提倡可持续性发展,这目前还是一个比较新的理念。达到全部指标可能短时间内无法完成。绿色建筑规范很多的时候是纪念馆,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大家都有意识了,包括园林搭建的回收、水池的防渗膜的利用、道路的回收系统,本身就是根据需要来设计,政策层面得到提升,设计师需要做的工作就是认真到位的贯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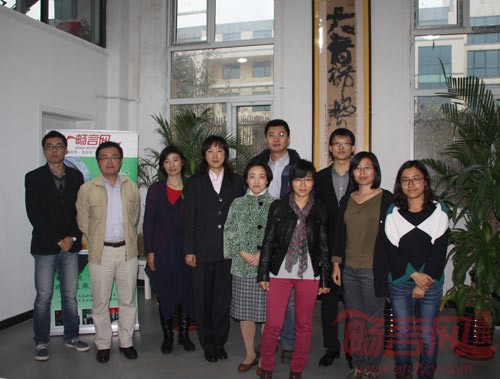
会后合影
幕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