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的很多规划方案不完善,不完善、不专业还管制,才是更大的灾害。”
“很多人的辨别能力有问题,回来什么都担忧,这个不敢那个不敢。留学生越多,这就越成问题。”
“10年前,许多人来新加坡都跟我说:‘你们太可怜,城市太枯燥。’我当时就说,不要听他们的,继续做我们自己的,城市骨架、功能、机理做好了,繁华会自动产生。”
“民意有两种,一种是当前人民和社会、企业真正的需要,这些需要其实民意会议上听不到,要自己去找、去理解。民意会议上谈的是另一种民意,就是个人利益。”
如今的中国就是个大工地。对于正在改造、更新中的中国城市来说,如何在政府、规划、民意之间寻找平衡,这似乎是一个极难求解的问题。
但在中国的政府官员们看来,一个现成的成功案例就放在那里——新加坡,这个上世纪70年代还凌乱不堪的小国,现在已经被称为“花园城市”。
刘太格可以说是新加坡经验的典型代表。他被称为“新加坡规划之父”,又是中国众多地区和城市的规划顾问,这恰恰说明,新加坡以及刘太格的规划思想已经被中国相当一部分官员所接纳。
刘太格说他的优势在于既了解西方,又了解东方,因而深深地懂得对于中国来说,现在究竟什么最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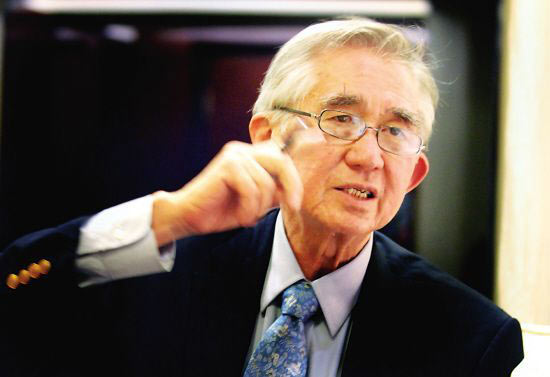
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先生(图片来源:百度)
政府理应承担更多责任
“虽然也在不停地进步,但和合理的规划还有距离”
南方周末:中国的很多官员到新加坡来学习城市规划和管理经验,在你看来,新加坡的这种成功有什么特殊之处?
刘太格:在规划方面,新加坡政府是承担了很大的责任,把规划做得很细,甚至每个地块的红线、容积率、高度控制、进出口都有规划。这种做法和西方、和中国都不同。
按照西方的理念,政府承担这么重大的责任、把地块规划做得这么细,就是不民主。在西方每个项目都要协商立场,他们甚至根本不同意要有规划。撒切尔夫人一上任就取消了所有的规划,当然现在又恢复了,因为他们发现,没有规划就没有办法控制环境、没有办法将城市梳理得比较协调和高效率。
我做过一个比喻,在任何一个城市拿一块地,如果找欧美人士来看,他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生活环境,因为他们没有快速发展的压力。而如果是亚洲人,他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利润,怎样尽可能取得最高的利益。新加坡是亚洲城市,在这方面是一样的,但新加坡又很侥幸,规划师把规划做得很细,尽量不留争议的余地。但一个规划局怎么能够把所有的事情都想那么细?不可能尽善尽美。所以新加坡是每五年一小改,十年一大改。每个项目在报批的时候可以提出规划方案的调整,不过能否调整不是一个人决定的,而是要通过一个委员会来决定,这一点不像中国。
南方周末:在你看来,中国的城市规划存在怎样的问题?
刘太格:在中国,首先是规划本身不健全,中国城市规划不过最近几十年的事情,做规划的人不一定完全理解城市运作是怎么回事。中国最近几十年和欧美人士有来往,可是他们的来往主要是片面的咨询,解决一个个地块的问题,而城市应该是大环境、宏观的处理。我见到中国规划师做的方案,虽然也在不停地进步,但和合理的规划还有距离。
南方周末:人们通常认为是政府官员不尊重规划,才会导致规划无法得到执行。你似乎把责任推到了规划师身上?
刘太格:在中国,许多政府官员当然不懂规划,他们对规划的理解是在上任之后边做边学的。关键是中国的很多所谓的规划专家自己对规划专业也不清楚,这怎么跟上司解释呢?他们唯一觉得懂的是建筑设计,于是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认为懂的领域,比如色彩、造型,这就变成长官和规划师干预建筑设计。这是不应该的,这样的问题应该让投资商和建筑师来处理。这样做,规划的政策和内容就太粗糙模糊,留下很多漏洞,开发商看到这些漏洞,当然就乘机而入,要求有优越的条件,要求提高地块的利润,利润的重要性自然超过环境。
新加坡虽然规划很详细,但基本不干预建筑设计,只有大概二十多个地块,因为是景观要点、视线走廊,我们要干预设计,但也并非规划师干预、政府干预,而是由当地资深建筑师组织委员会去干预。这是比较科学化的做法,既要干预,又要尊重专家意见,不要政府自己全包下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