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性建筑师事务所存在的价值及其最重要的特点在于探索性。
这种探索性体现在作为一个学科的建筑学本体语言和方法的创新。这样,他们的设计必然会与同时期行业内通常的观念和方法保持距离,而通过实践对相关学科、行业产生积极影响。
但探索性建筑师事务所也必须向业主提供作为一个职业建筑师应当提供的相应服务;需要稳定的经济收入以支撑事务所的生存和发展。所以,他们需要寻找并创造能够使自己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土壤,并在相应社会土壤中扎根。
鉴于土壤本身的特征和扎根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会在事务所及其作品里面留下鲜明的痕迹,本文不使用“实验性”这一十年来更常用的表述,而回归更早的提法——“探索性”。
2000-2002年家琨建筑、都市实践、马达思班、大舍等事务所的相继成立,显示探索性建筑师事务所开始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在建筑设计行业,至今已经十年。这十年,探索性建筑师事务所是如何在社会土壤中扎根的呢?

群体声音——从展览到集群建筑
建筑展览是推广建筑设计行业探索性成果,并传播相关价值观和思考方式的重要手段。但对于探索性建筑师事务所来说,近十年来,展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将若干个体的事务所通过展览活动,以群体的形象展示在公众面前,以此将相对微弱的声音加以强化。
1999年“中国青年建筑师实验性作品展”的出现有一定的偶然性,展出作品的定位和价值观还不够明确,但展览塑造了以“实验建筑”为特色的新一代建筑师群体的基本形象和话语方式。如展览的组织者之一王明贤所说:“我发现一部当代建筑史和我们距离是这么近,我们的行动本身就是当代建筑史的一部分。”而2001年德国柏林的“土木”中国新建筑展则使这个群体的定位和价值取向明确化。后来的深港双年展等活动,每次策展人风格都有明显差别,但在每次展览价值取向的明显差异中,这个群体的特征反而更加清晰,更加稳定。
展览的焦点在于发出群体性声音,那么作为事件,展览本身要在短时间内聚集人们的注意力,然后在集中的关注退去之后,渐渐发酵,并在行业的发展中留下或多或少的痕迹。而相比之下,同样是群体性声音,集群建筑的影响力则更加长久,而其运作周期更长、环节更多,更需要社会性力量的支撑。
集群建筑是西方现代主义早期,作为先锋派的现代主义建筑师发出自己群体性声音的重要方式。1925年斯图加特的魏森霍夫住宅展就是其中最著名的实例。后来这种模式在世界各地多次被仿效。
与魏森霍夫住宅展由当时魏玛共和国强势的斯图加特地方政府和工业家们联合德意志制造联盟主办不同,中国第一次成功的集群建筑运作——长城脚下的公社却选择了开发商作为合作者。世纪之交,作为在当时中国迅速崛起,并渴望在商业之外的领域发出自己声音的开发商代表——潘石屹,策划组织的这次活动,既成功树立了自己作为艺术赞助人的声誉和地位,又为中外各种探索性建筑师事务所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更重要的是,潘石屹作为开发商中有影响的人物,成功将确立相应形式语言和价值观在甲方和建筑师群体头脑中的一席之地。
这种运作方式的特点是:开发商出资,并以获得自身的声誉和广告效应为目的;建筑师获得实现自己心目中理想作品的机会,但出于广告效应的目的,对其形式语言的要求远远大于其他要素。后来其他的集群建筑运作虽然细节上有所差异,但都相对忽视建成后集群建筑运作模式的经济性和合理性。所以,与魏森霍夫住宅展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不同,中国相应的集群建筑策划缺乏介入社会层面的深度。而在资本的运作下,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理念再引进的探索性建筑,被包装上了一层高档化、精英化的外衣,导向反而与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理念相反。

双重实践——生存的权宜和折衷
在当代中国,低设计费标准与低设计完成度支撑着大量性建造的背景。探索性建筑作品面对作为一个学科的建筑学,必然要求更完整的设计理念和更高的完成度,这样便与低设计费标准产生了矛盾。尽管展览和集群建筑使这个群体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并受到社会的关注,但相应的市场容量却很有限。这迫使很多探索性建筑师事务所采取了双重实践的生存方式:即通过大量性作品维持事务所经济上的生存和发展,通过探索性作品在学科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获得相应的一席之地。这种生存的权宜与折衷,至少在探索性建筑师事务所创立的初期有相当的普遍性和代表性。
这也是一种扎根,虽然充满无奈,但至少表现了一种追求的信念和坚韧。
改变这种局面的转机是存在的,但已经不带有群体性特点,而成为特定建筑师事务所的个体事件了。
一些在特定类型建筑设计上的的探索,有可能因为社会需求合拍而被主流所接受,这是探索性建筑师事务所面临最重要的机遇。马达思班建筑师事务所在宁波完成的天一广场,所展现的一种新的商业建筑设计思路引起很多开发商的兴趣,确立了其在商业建筑设计领域的地位;同样,青浦夏雨幼儿园也为大舍获得了更多的幼儿园设计委托。这些不但有助于建筑师在实践中将原来的探索性思路进一步推向成熟,更使事务所的探索和经济上的生存发展获得了难得的统一。
当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很多探索性建筑师事务所面临着向主流的转型。这在国际上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日本的丹下健三事务所就是成功的例子之一。其实,探索在成熟后走向主流是建筑设计行业良性运作的证明,如果探索与主流永远保持距离反而体现着一些问题。主流建筑师事务所维持足够的探索性更有利于中国建筑整体设计水准的提高。
另外,一些建筑师事务所积极将其建筑探索与社会需求结合,获得了若干难得的突破。都市实践对城中村改造的探讨,在大芬美术馆中得到了部分(虽然很有限)的实现。而其与万科合作的土楼公舍得以完成则显得更加重要,这个作品提出了解决居住问题的其他可能性。
探索性建筑师事务所初期生存的困境不仅仅出现在当代中国。但当代中国大片土地开发的模式,在一片片建筑拔地而起的同时,自建小住宅的设计业务却相当有限。而自建小住宅往往是欧美和日本探索性建筑师事务所初期的主要业务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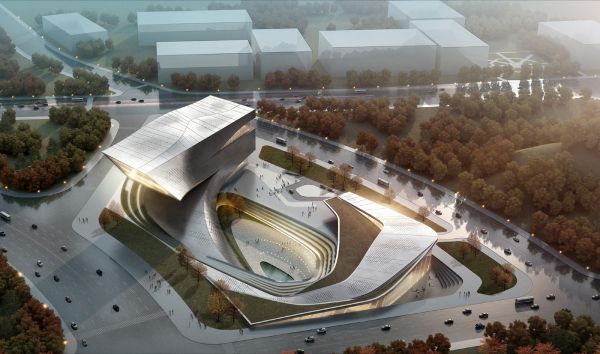
外向生存——全球化背景下的另一种选择
中国建筑界曾经封闭;后来有了窗,我们可以看到外面,外面也可以看到我们;接着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外面的人也可以进来。而现在,墙也开始慢慢地消解。在与世界建筑界交往和互动越来越多的今天,我们完全有可能人在中国,却参与世界范围内的建筑活动。这就是以MAD和侯梁建筑师事务所为代表的新一代建筑师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另一种选择。
对于有着海外留学背景的马岩松和侯梁等人来说,这也是一种扎根,只不过根系在世界范围内。MAD在加拿大多伦多ABSOLUTE超高层公寓设计竞赛中拔得头筹,侯梁建筑师事务所在多次国际建筑竞赛中入围都表明了这种外向生存方式的可能性。目前这两个探索性建筑师事务所都获得了更多来自境外的设计委托。
前OMA北京办事处的主管奥雷•舍人说:“如今中国处于高速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外国建筑师来到中国,协助建设这个现代化进程,并带来不同的文化和专业技术,相信中国的建筑师很快也能到国外去,将所学用于在外国的建设,很快将这一状况扭转过来。事实上,已经有新一代的中国建筑师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我在几年前写的评论侯梁建筑师事务所的文字也提到:“在全球化背景下参与全球建筑实践也可以成为中国建筑师的一种选择。如果仿照陈丹青的说法,把世界当代建筑史比做一张集体照的话,那么,若干年后,如果有几位中国建筑师的身影出现在诸如前排左起第几位那样的位置上,也是作为中国建筑师整体的一种荣耀。”
|




